德性伦理学 简介-Blues的文章 Introduction to Virtue Ethics
An introduction to virtue ethics, emphasizing virtue and character as the primary subject of ethics
tags: zhihu-article zhihu-link: https://zhuanlan.zhihu.com/p/1903915407682827083
德性伦理学(亦称“美德伦理学”[注a][1],源自希腊文 ἀρετή [aretḗ])是一种哲学方法,它将德性(virtue)和品格(character)视为伦理学的首要主题,这与其他将自愿行为的后果、行为准则或规则,或对神圣权威的服从置于首要地位的伦理体系形成对比。[2]
德性伦理学通常与伦理学中的另外两种主要方法——后果主义(consequentialism)和义务论(deontology)——相对照,前者强调行为结果的“善”(consequentialism),后者则以道德义务的概念(deontology)为核心。尽管德性伦理学不一定否认事态的善或道德义务对伦理学的重要性,但它强调德性,有时还强调其他概念(如“幸福”eudaimonia),其强调程度是其他伦理学理论所不及的。[来源请求]
核心概念 德性与恶习 主要文章:德性 与 道德品格 在德性伦理学中,德性(virtue)是在生活的某个领域中良好思考、感受和行动的性格倾向。[3] 相反,恶习(vice)则是在生活的某个领域中不良思考、感受和行动的性格倾向。德性并非日常习惯;它们是性格特质,因为它们对一个人的个性和其为人至关重要。
在早期版本和一些现代版本的德性伦理学中,德性被定义为一种能够促进或展现拥有者“人的繁荣与福祉”(human “flourishing and well being”)的性格特质。[4] 一些现代版本的德性伦理学不以福祉或繁荣来定义德性,有些甚至将德性定义为倾向于促进某种独立于德性本身定义的其他“善”的特质,从而将德性伦理学归入(或以某种方式合并于)后果主义伦理学之下。[5]
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德性并非一种使人更能实现“幸福”(eudaimonia)的技能,它本身就是“幸福”的体现——活动中的“幸福”。[6]
与后果主义和义务论伦理体系(在这些体系中,即使不符合自身利益,个体也可能被要求做正确的事——相反,他是为了更大的善或出于义务而做)相反,在德性伦理学中,人做正确的事是因为这符合其自身利益。实践德性伦理学训练的一部分,是让人认识到个人开明的自利与践行德性之间的一致性,从而使人自愿地、欣然地、热情地践行德性,因为他知道有德性是人能为自己做的最好的事情。[7]:I
德性与情感 在古希腊和现代的以“幸福”(eudaimonic)为导向的德性伦理学中,德性与恶习是复杂的倾向,既包含情感成分也包含理智成分。[8] 也就是说,它们是既能对正确行为进行良好推理(参见下文关于“明智”phronesis的论述),又能正确运用情感和感受的倾向。
例如,一个慷慨的人能够很好地推理何时以及如何帮助他人,并且此人也乐于助人且没有内心冲突。在这方面,有德性的人不仅与恶劣的人(对该做什么推理不当,且情感上依恋错误事物的人)和意志薄弱的人(尽管知道什么是对的,却被情感诱惑去做错事的人)形成对比,也与仅仅自制的人(其情感诱使他们做错事,但其意志力让他们做了他们知道是正确的事)形成对比。
根据罗莎琳·赫斯特豪斯(Rosalind Hursthouse)的观点,在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中,情感具有道德意义,因为“德性(和恶习)不仅是行动的倾向,也是感受情感的倾向,既是反应也是行动的冲动……[并且]在有德性的人身上,这些情感会在正确的场合、针对正确的人或对象、出于正确的原因而感受到,这里的‘正确’意味着‘恰当’……”[9]
明智(Phronesis)与幸福(Eudaimonia) 明智(Phronesis,φρόνησις;审慎、实践德性或实践智慧)是一种后天习得的特质,使其拥有者能够在任何给定情境中辨别出最佳行动方案。[10] 与理论智慧不同,实践理性导致行动或决策。[11] 正如约翰·麦克道尔(John McDowell)所言,实践智慧包含对情境所要求的“感知敏感性”。[12]
幸福(Eudaimonia,εὐδαιμονία)是一个源自希腊语的词,常被翻译为“福祉”、“快乐”、“至福”,在德性伦理学语境下则为“人的繁荣”。[13] 在此意义上,“幸福”不是一种主观状态,而是一种客观状态。[来源请求] 它描绘了“过得好的生活”。
根据亚里士多德——西方哲学传统中“幸福”概念最杰出的阐释者——的观点,“幸福”定义了人生的目标。它在于运用人类特有的品质——理性——作为灵魂最恰当和最具滋养性的活动。在其《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如同之前的柏拉图)认为,追求“幸福”是“灵魂合乎完美德性的活动”,[7]:I 这种活动只能在人类特有的社群——城邦(polis)中得到恰当的实践。[14]
尽管“幸福”最初由亚里士多德普及,但它现在已普遍属于德性理论的传统。[15] 对于德性理论家而言,“幸福”描述了过着合宜人生的个体所达到的状态,这一结果可以通过践行德性来达到。德性是一种习惯或品质,使其拥有者能够成功实现其目的。例如,刀的德性是锋利;赛马的德性之一是速度。因此,要确定人类的德性,就必须对人类的目的是什么有所说明。
并非所有现代德性伦理学理论都是以“幸福”为导向的;有些理论用其他目的取代“幸福”,而另一些则是非目的论的:也就是说,它们不根据践行德性所产生或倾向于产生的结果来解释德性。[16]
德性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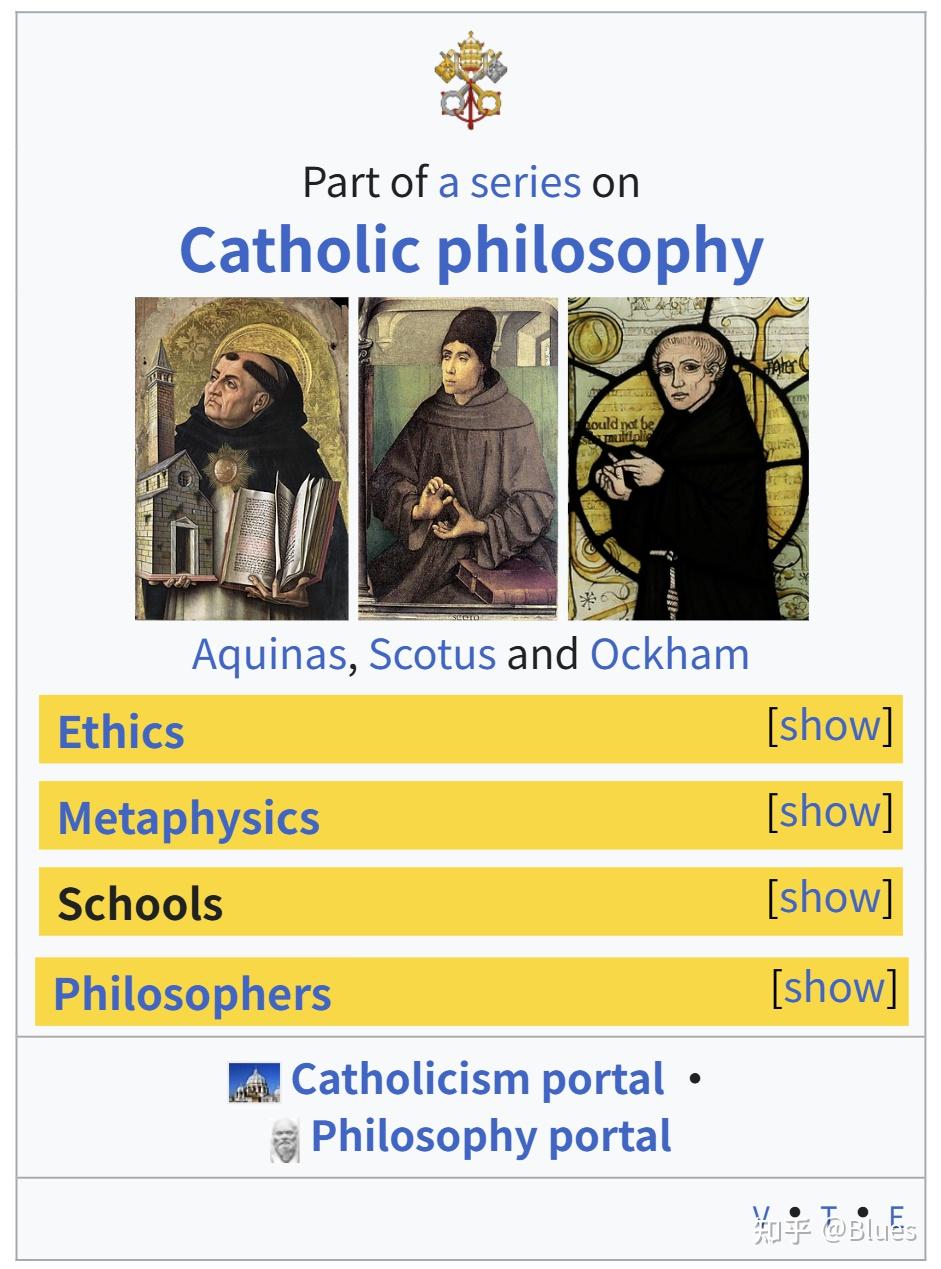
与西方传统的大部分内容一样,德性理论起源于古希腊哲学。
德性伦理学始于苏格拉底,后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学派进一步发展。[17] 德性伦理学关注个体的品格,而非个体的行为(或其后果)。关于哪些具体德性值得称赞,德性伦理学的拥护者之间存在争论。然而,大多数理论家都同意,伦理是通过践行德性来体现的。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德性的处理方式不尽相同。柏拉图认为德性实际上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目的,朋友可能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有用手段。亚里士多德则指出,德性的功能更像是维护人际关系的手段,尤其是真挚的友谊,没有友谊,人对幸福的追求就会受挫。
对所谓四主德——智慧、正义、坚韧和节制——的讨论可见于柏拉图的《理想国》。德性在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伦理理论中也占据显著地位。[7]
德性理论被李维(Livy)、普鲁塔克(Plutarch)和塔西佗(Tacitus)等道德主义历史学家引入历史研究。希腊的德性观念通过西塞罗(Cicero)传入罗马哲学,后由米兰的安波罗修(Ambrose of Milan)融入基督教道德神学。在经院哲学时期,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在其《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e)和《尼各马可伦理学评注》(Commentaries on the Nicomachean Ethics)中对德性进行了最全面的神学探讨。[18]
宗教改革后,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在17世纪末之前一直是新教大学伦理学学科的主要权威,在1682年之前,已有超过五十部关于《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新教评注出版。[19]
尽管这一传统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在欧洲哲学思想中退居幕后,但“德性”一词在此期间仍然流行,并实际上在古典共和主义或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中占据显要位置。这一传统在16世纪的意大利以及17、18世纪的英国和美国的思想界占据重要地位;实际上,“德性”一词频繁出现在托马斯·费尔南德斯·德·梅德拉诺(Tomás Fernández de Medrano)、尼可罗·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大卫·休谟(David Hume)、英国内战时期的共和主义者、18世纪英国辉格党人以及苏格兰启蒙运动和美国开国元勋中的杰出人物的著作中。
当代的“德性转向” 尽管一些启蒙哲学家(如休谟)继续强调德性,但随着功利主义和义务论伦理学的兴起,德性理论在西方哲学中逐渐被边缘化。德性理论的当代复兴通常追溯至哲学家伊丽莎白·安斯康姆(Elizabeth Anscombe)1958年的论文《现代道德哲学》(Modern Moral Philosophy)。[20] 此后:
- 在1976年的论文《现代伦理理论的精神分裂》(The Schizophrenia of Modern Ethical Theories)中,迈克尔·斯托克(Michael Stocker)总结了德性伦理学对义务论和后果主义伦理学的主要批评。[21]
- 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百科全书编纂者莫蒂默·阿德勒(Mortimer Adler)在其已出版的著作中始终诉诸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以及幸福或“eudaimonia”的德性理论。
- 菲利帕·富特(Philippa Foot)于1978年出版了一本题为《德性与恶习》(Virtues and Vices)的论文集。[22]
- 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致力于在与现代和后现代思想问题的对话中重建一种基于德性的理论;其著作包括《德性之后》(After Virtue)和《道德探究的三种对立版本》(Three Rival Versions of Moral Enquiry)。[23]
- 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在其主体的解释学现象学中,尤其是在其著作《作为他者的自身》(Oneself as Another)中,给予了亚里士多德目的论伦理学重要地位。[24]
- 神学家斯坦利·哈耶瓦斯(Stanley Hauerwas)发现德性的语言对其自身的研究项目有所助益。
- 理查德·泰勒(Richard Taylor)在其著作《德性伦理学导论》(Virtue Ethics An Introduction,1991)中主张恢复古典德性作为道德的基础。[25][26]
- 罗杰·克里斯普(Roger Crisp)和迈克尔·斯洛特(Michael Slote)编辑了一本名为《德性伦理学》(Virtue Ethics)的重要论文集。[27]
- 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和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理论化国际发展的能力方法时运用了德性理论。
- 朱莉娅·安纳斯(Julia Annas)撰写了《幸福的道德》(The Morality of Happiness,1993)。[28]
- 劳伦斯·C·贝克尔(Lawrence C. Becker)在《新斯多葛主义》(A New Stoicism,1998)中将当前的德性理论与古希腊斯多葛主义联系起来。[29]
- 罗莎琳·赫斯特豪斯(Rosalind Hursthouse)出版了《论德性伦理学》(On Virtue Ethics,1999)。[30]
- 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在概念化积极心理学时借鉴了古典德性伦理学。
- 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在其关于情商的书中以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一个挑战开篇。[31]
- 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在其著作《正义:什么是正确的做法?》(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中讨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以支持其关于正义的伦理理论。
道德哲学中的“德性转向”(aretaic turn)与其他哲学学科中的类似发展并行。其中之一是认识论,琳达·扎格泽布斯基(Linda Zagzebski)等人在此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德性认识论。在政治理论中,出现了对“德性政治”的讨论,而在法律理论中,关于德性法理学的文献虽少但日益增多。“德性转向”也存在于美国宪法理论中,其支持者主张强调宪法裁判者的德性与恶习[需澄清]。[来源请求]
对道德、认识论和法理学的德性方法一直是激烈辩论的主题。一种批评集中于指导性问题;反对者罗伯特·劳登(Robert Louden)在其文章《德性伦理学的某些缺陷》(Some Vices of Virtue Ethics)中质疑,一个有德性的道德行为者、信徒或法官的观念是否能为行动、信念形成或法律纠纷的解决提供必要的指导。[32]
德性清单 存在多种德性清单。苏格拉底认为德性即知识,这意味着实际上只有一种德性。[33] 斯多葛学派确定了四种基本德性:智慧、正义、勇敢和节制。智慧细分为良好判断力、良好计算能力、机敏、审慎和足智多谋。正义细分为虔诚、诚实、衡平(equity)和公平交易。勇敢细分为忍耐、自信、高尚、乐观和勤奋。节制或适度细分为良好纪律、得体、谦逊和自控。[34]
约翰·麦克道尔(John McDowell)认为,德性是一种“感知能力”,用以辨别应该如何行动,所有特定的德性都仅仅是对一系列行动理由的“专门敏感性”。[35]
亚里士多德的清单 亚里士多德确定了12种德性,这些德性表明一个人正在良好地履行其作为人的功能。[7] 他区分了与情感和欲望相关的德性以及与心智相关的德性。[7]:II 前者他称为道德德性,后者称为理智德性(尽管在现代意义上两者都属于“道德”范畴)。
道德德性 亚里士多德提出,每种道德德性都是两种相应恶习——一种过度,一种不足——之间的“中道”(golden mean)。每种理智德性都是一种心智技能或习惯,通过它,心智达到真理,肯定其所是或否定其所非。[7]:VI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他讨论了11种道德德性:
| 维度 | 过度 | 中道 (Golden mean) | 不足 |
|---|---|---|---|
| 恐惧与信心 | 鲁莽 | 面对恐惧时的勇敢[7]:III.6–9 | 怯懦 |
| 快乐与痛苦 | 放纵 | 面对快乐与痛苦时的节制[7]:III.10–12 | 麻木不仁 |
| 获取与花费(小额) | 挥霍 | 对财富和财产的慷慨[7]:IV.1 | 吝啬 |
| 获取与花费(大额) | 粗鄙 | 对巨额财富和财产的恢弘[7]:IV.2 | 寒酸 |
| 荣誉与不名誉(重大) | 虚荣 | 对重大荣誉的大度[7]:IV.3 | 卑怯 |
| 荣誉与不名誉(普通) | 空虚的虚荣 | 对普通荣誉的适度抱负[7]:IV.4 | 胸无大志 |
| 愤怒 | 易怒 | 忍耐/温和[7]:IV.5 | 缺乏精神/麻木 |
| 自我表达 | 自夸 | 自我表达的诚实[7]:IV.7 | 过度谦虚 |
| 交谈 | 滑稽 | 交谈中的风趣[7]:IV.8 | 粗野 |
| 社会行为 | 谄媚 | 社会行为中的友善[7]:IV.6 | 乖戾 |
| 义愤 | 嫉妒 | 面对伤害时的正义与义愤[7]:IV.5 (此条目原文可能指对他人不幸的幸灾乐祸为恶,义愤为中道,嫉妒为不足,但通常嫉妒与幸灾乐祸都视为恶。此处按原文翻译,但需注意其复杂性) | 幸灾乐祸/恶意 |
理智德性 努斯(Nous,理智/直观理性),把握基本真理(如定义、自明原则)[7]:VI.11 认知(Episteme,科学知识),是具有推理性推理的技能(如证明、三段论、论证)[7]:VI.6 * 索菲亚(Sophia,理论智慧),将基本真理与有效、必然的推论相结合,以对不变的真理进行良好推理。[7]:VI.5
亚里士多德还提到了其他一些特质: 格诺梅(Gnome,良好判断力)——做出判断,“同情的理解”[7]:VI.11 领悟(Synesis,理解力)——理解他人所说,不发出命令 明智(Phronesis,实践智慧)——知道该做什么,关于变化真理的知识,发出命令[7]:VI.8 技艺(Techne,艺术、手艺)[7]:VI.4
然而,亚里士多德的清单并非唯一的清单。正如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在《德性之后》中观察到的,像荷马(Homer)、新约作者、托马斯·阿奎那和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这样形形色色的思想家都提出过德性清单。[36] 沃尔特·考夫曼(Walter Kaufmann)提出了四种基本德性:雄心/谦逊(“谦卑雄心”,humbition)、爱、勇敢和诚实。[37]
批评 德性理论的支持者[何人?]有时认为,德性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其普遍适用性。换言之,任何被定义为德性的性格特质,都必须合理地被普遍认为是所有人的德性。根据这种观点,例如,声称奴性是女性的德性,同时又不将其作为男性的德性,这是不一致的。[38]
其他德性理论的支持者,特别是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对此反驳道,任何关于德性的解释都必须产生于那些德性将被实践的社群之中:伦理学(ethics)一词本身就暗示了“风俗”(ethos)。也就是说,德性是,而且必须是,植根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的。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德性标准,对于公元21世纪多伦多的恰当行为来说,会是一个荒谬的指南,反之亦然。持这种观点并不一定意味着德性的解释因此必须是静态的:道德活动——即思考和实践德性的尝试——可以提供文化资源,使人们能够(尽管缓慢地)改变他们自己社会的风俗。
麦金太尔在其关于德性伦理学的开创性著作《德性之后》中似乎持此立场。
对德性理论的另一个反对意见[何人的?]是,德性伦理学不关注哪些行为在道德上是允许的,哪些是不允许的,而是关注一个人应该培养什么样的品质才能成为一个好人。换言之,虽然一些德性理论家[何人?]可能不会谴责例如谋杀本身是一种不道德或不被允许的行为,但他们可能会认为,犯下谋杀罪的人严重缺乏几种重要的德性,如同情心和公平。尽管如此,理论的反对者[何人?]常常反对说,理论的这一特性使得德性伦理学作为一种适合作为立法基础的普遍行为规范是无用的[来源请求]。一些德性理论家[何人?]承认这一点,但他们的回应是反对合法立法权威的概念本身,实际上主张某种形式的无政府主义作为政治理想[来源请求]。其他德性理论家[何人?]则认为法律应由有德性的立法者制定,还有另一组人则认为,有可能将司法系统建立在德性的道德观念而非规则之上。亚里士多德本人将其《尼各马可伦理学》视为其《政治学》的前篇,并认为政治的意义在于为有德性的公民的发展创造肥沃的土壤,而德性的一个目的在于它有助于为健康的城邦做出贡献。[7]:X.9[14]
一些德性理论家[何人?]可能会以“坏行为”也是具有恶习特征的行为这一观念来回应这一总体反对意见[来源请求]。也就是说,那些不以德性为目标,或偏离德性的行为,将构成我们对“坏行为”的理解。虽然并非所有德性伦理学家都同意这一观念,但这是德性伦理学家重新引入“道德上不允许”概念的一种方式。人们可能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种观点犯了“诉诸无知”的逻辑谬误,因为它假定,凡非德性的就是不道德的。换言之,仅仅因为一个行为或人“缺乏德性的证据”,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并不意味着该行为或人就是不道德的。
被义务论和功利主义所包含 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提出,尽管德性伦理学常被认为是反启蒙的,“怀疑理论并尊重地方实践中体现的智慧”,[39] 但它实际上既不与义务论和功利主义有根本区别,也不能算作它们的对立方法。她认为,这两大启蒙传统的哲学家经常包含德性理论。她指出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中的“德性学说”(Doctrine of Virtue)“涵盖了与古希腊经典理论大部分相同的主题”,“他提供了一种关于德性的普遍解释,即意志在克服任性和自私倾向方面的力量;他详细分析了诸如勇敢和自制等标准德性,以及贪婪、撒谎、奴性和骄傲等恶习;尽管他通常将倾向描绘成与德性对立,但他也认识到同情的倾向为德性提供了关键支持,并敦促人们刻意培养这些倾向。”[39]
努斯鲍姆还指出了功利主义者如亨利·西奇威克(Henry Sidgwick,《伦理学方法》The Methods of Ethics)、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和约翰·斯图亚트·密尔(John Stuart Mill)对德性的考量,后者在为女性道德平等辩护(《妇女的屈从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时谈到了道德发展。她认为,当代的德性伦理学家如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菲利帕·富特和约翰·麦克道尔几乎没有共同观点,他们工作的核心内容也并不代表与康德的决裂。
康德的批判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对德性伦理学的立场存在争议。认为康德义务论与德性伦理学冲突的人包括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菲利帕·富特和伯纳德·威廉姆斯。[40] 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和《实践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中,伊曼努尔·康德对之前的伦理框架和道德理论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批评[来源请求]。康德很少点名亚里士多德,但并未将其德性伦理学的道德哲学排除在其批判之外。许多康德主义者反对德性伦理学的论点声称,德性伦理学是不一致的,或者有时它根本不是一种真正的道德理论。[41]
在《德性伦理学究竟是什么?》(What Is Virtue Ethics All About?)[42]一文中,格雷戈里·贝拉斯科·伊·特里亚诺斯基(Gregory Velazco y Trianosky)指出了德性伦理学家与他所谓的“新康德主义”之间的主要分歧点,表现为以下九种新康德主义的道德主张:
- 关键的道德问题是“做什么是正确/必须的?”
- 道德判断是那些关乎行为正确性的判断。
- 此类判断采取规则或原则的形式。
- 此类规则或原则是普遍的,不因人而异。
- 它们并非基于某种独立于道德善的人类善概念。
- 它们采取绝对命令的形式,这种命令的证成独立于其适用对象的欲望。
- 它们具有激励作用;它们可以迫使行为者行动,同样独立于该行为者的欲望。
- 一个行为,为了在道德上具有德性,必须受此类道德判断的激励(例如,不仅仅是碰巧与之相符)。
- 性格特质或德性的“德性”源于该特质与道德判断、规则和原则的关系。
特里亚诺斯基说,现代德性伦理学的同情者几乎都拒绝新康德主义的主张#1,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拒绝其他一些主张。
乌托邦主义与多元主义 罗伯特·B·劳登(Robert B. Louden)批评德性伦理学,认为它推崇一种不可持续的乌托邦主义。在当代社会,试图达成一套单一的德性标准是极其困难的,因为据劳登所言,这些社会包含“比亚里士多德理论中的道德社群更多的民族、宗教和阶级群体”,而这些群体“不仅有其自身的利益,也有其自身的德性体系”。劳登顺便提到,麦金太尔这位基于德性的伦理学的支持者,在《德性之后》中已经探讨了这个问题,但他认为伦理学不能放弃围绕行为建立规则,而仅仅依赖于讨论人的道德品格。[43]
德性伦理学中的议题 作为一种范畴的德性伦理学 更多信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书籍)和论自由 德性伦理学与义务论伦理学和后果主义伦理学形成对比;这三者是当代最主要的规范伦理学理论。义务论伦理学,有时被称为责任伦理学,强调遵守伦理原则或责任。然而,这些责任如何定义,常常是争论的主题。义务论者使用的一种规则体系是神命论(divine command theory)。义务论也依赖于元伦理实在论(meta-ethical realism),假定无论环境如何,都存在道德绝对性。伊曼努尔·康德被认为是义务论伦理学的最重要理论家。
规范伦理学中下一个主要的思想流派是后果主义。义务论强调尽职,而后果主义则将行为的道德性建立在其结果之上。后果主义者不会说一个人有道德义务不杀人,而是会说我们应该避免杀人,因为它会产生不良后果。主要的争论点在于哪些结果应该(或可以)被确定为客观上可取的。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最大幸福原则是一个普遍采用的关于何为客观上可取的标准。密尔断言,行为的可取性在于它带来的幸福净量、它给多少人带来幸福以及幸福的持续时间。他试图划分幸福的类别,有些类别优于其他类别,但对此类概念进行分类是困难的。
德性伦理学家确定有德性的人所体现的德性(亦称可取特质)。展现这些德性是伦理学的目标,而一个人的行为是其德性的反映。对德性哲学家而言,行为不能作为道德的划分标准,因为德性不仅仅是对行为的选择;它是一种存在方式,引导展现德性的人持续做出特定类型的选择。德性伦理学内部对于哪些是德性,哪些不是,存在分歧。在所有情况下确定要采取的“有德性的”行为,以及如何定义德性,也存在困难。
后果主义和义务论理论通常仍在一个受限的意义上使用“德性”一词:即遵守系统原则或规则的倾向(或习性)。在这些理论中,德性是次要的,原则(或规则)是首要的。对“德性”构成要素的这些不同理解是潜在混淆的来源。[44] 关于人生目的或人类美好生活的教条式主张通常具有争议性。
德性与政治 德性理论强调亚里士多德的信念,即城邦(polis)是政治组织的顶峰[来源请求],以及德性在使人类在该环境中繁荣发展方面的作用。相反,古典共和主义强调塔西佗的担忧,即权力和奢侈会腐蚀个人并摧毁自由,正如塔西佗在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转变过程中所察觉到的那样。对古典共和主义者而言,德性是抵御此类腐败的盾牌,是维护已拥有的美好生活的手段,而不是实现尚未拥有的美好生活的手段。另一种表述两者区别的方式是,德性伦理学依赖于亚里士多德关于“人之实然”(human-being-as-he-is)与“人之应然”(human-being-as-he-should-be)的基本区分,而古典共和主义则依赖于塔西佗关于“演变成……的风险”(risk-of-becoming)的区分。[45]
德性伦理学有许多当代应用:
社会与政治哲学 在社会伦理学领域,戴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认为,德性伦理学可以为理解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一个平衡方法的基础。[46][47]
教育 在教育哲学领域,詹姆斯·佩奇(James Page)认为,德性伦理学可以为和平教育提供理论依据和基础。[48]
医疗保健与医学伦理 托马斯·阿卢雷德·福恩斯(Thomas Alured Faunce)认为,如果医疗环境中的“吹哨行为”(whistleblowing)在德性伦理学中有更坚实的学术基础,那么它在临床治理途径中会更受尊重。[49] 他呼吁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生物伦理与人权宣言》中明确支持“吹哨行为”。[50] 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认为,“实践智慧”是现代医疗保健系统中许多低效和不人道官僚主义的解毒剂。[51]
技术与德性 香农·瓦勒(Shannon Vallor)在其著作《技术与德性》(Technology and the Virtues)[52]中提出了一系列“技术道德”德性,人们需要在我们的社会技术世界中培养这些德性才能繁荣发展:诚实(尊重真理)、自制(成为我们欲望的主人)、谦逊(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正义(坚持正当)、勇敢(明智的恐惧与希望)、同情(对他人的慈悲关怀)、关爱(对他人的爱心服务)、文明(共创事业)、灵活性(对变化的熟练适应)、洞察力(把握道德整体)和恢弘(道德领导力与精神高贵)。
参见 应用伦理学 – 道德考量的实际应用 卓越/美德 (Arete) – 希腊哲学概念 佛教伦理学 (学科) 儒家思想 – 中国伦理与哲学体系 犬儒主义 (哲学) – 古代哲学学派 环境德性伦理学 – 通过德性伦理学视角探讨环境伦理学的方法 现代斯多葛主义 – 以德性为核心的哲学体系 明智 (Phronesis) – 古希腊语中指一种智慧或才智的词 依高层法而治 – 认为普世道德原则高于不公正法律的信念 七德 – 基督教传统中的七种德性 斯多葛主义 – 以德性为核心的哲学体系 《蒂鲁古拉尔》 (Tirukkuṟaḷ) – 关于个人伦理与道德的古泰米尔文献 德性认识论 – 一种哲学方法 德性法理学 – 应用于法理学的德性伦理学 * 德性信号 – 贬义词
- Applied ethics –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moral considerations
- Arete – Greek philosophical concept
- Buddhist ethics (discipline)
- Confucianism – Chinese ethical and philosophical system
- Cynicism (philosophy) – Ancient school of philosophy
- Environmental virtue ethics – Way of approaching environmental ethics through the lens of virtue ethics
- Modern Stoicism – Virtue-focused philosophical system
- Phronesis – Ancient Greek word for a type of wisdom or intelligence
- Rule according to higher law – Belief that universal principles of morality override unjust laws
- Seven virtues – Seven virtues in Christian tradition
- Stoicism – Virtue-focused philosophical system
- Tirukkuṟaḷ – Ancient Tamil composition on personal ethics and morality
- Virtue epistemology – Philosophical approach
- Virtue jurisprudence – Virtue ethics applied to jurisprudence
- Virtue signalling – Pejorative term
注释 a. 发音:/ˌærəˈteɪ.ɪk/。
for references, further reading and external links, please visit
translated by Gemini 2.5 pro in one shot and can be used for evaluating model’s long-text ability